
因为她的短篇小说集中译本出版,爱尔兰作家露西·考德威尔来到上海书展,她个子高挑,在人群中像一只高冷的白鹭。但是当她开口,声音轻柔温和,语速如抒情的慢板,和她讨论写作经验,与阅读她小说的体验是相似的,是既私密又带来力量感的“呼喊与细语”。

她的短篇小说集《所有人都刻薄又邪恶》获2021年BBC英国短篇小说奖,在那之前,她的长篇小说和原创剧本陆续获得爱尔兰作家与剧作家工会奖、英联邦作家奖。她形容自己经历10年创作摸索到短篇小说的秘密:“它们不是短故事,反而接近于时刻牵动观众心绪的独白剧场。”她乐于听到这些小说被评价“似乎什么都没发生,又触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写作的意义在于照亮现实中“微不足道的小事”,所有被忽略的瞬间组成关于当代人的精神世界“立体主义肖像”。当她了解到中译本因为语言的差异和特性,放大了她小说中“心理漫游”的现代气质,她惊喜不已:“英语诗歌的现代主义写作始于艾略特,他是受到埃兹拉·庞德的启发,而庞德的重要灵感来源是李白的诗!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想到我能在自己的作品里见证中文和英文、中国文学和英语文学的奇妙化学反应。”
书写女性经验就像“总也做不完的家务”
《留在这个世界的理由》和《所有人都刻薄又邪恶》覆盖了女性从青春期到初为人母的各种“不足为外人道”的遭遇以及内心体验。露西写初中女孩为了摆脱被同学孤立的隐形霸凌,与“声名狼藉”的女孩结成别扭的友谊,为了吹嘘自己的“女性魅力”,她们接二连三作出幼稚荒唐的傻事,险遭性侵;她写荷尔蒙涌动的高中女孩对中年男老师产生莫名激情,多年以后她偶然遇见老迈的老师仍和十几岁的女孩约会,痛苦地看清对方是“狩猎”的惯犯;她写年轻母亲在公共场合里一时找不到孩子,片刻陷入歇斯底里的癔症,短短几十秒里想象自己将度过支离破碎的一生,当孩子重新出现在视野中,她才明白虚惊一场;她写养育女儿的母亲们回忆大学时代女生之间对莱文斯基的荡妇审判,当她们以姐姐的、母亲的心态回看“丑闻中的女孩莱文斯基”,开始忏悔并反思女性对女性、女性对社会风俗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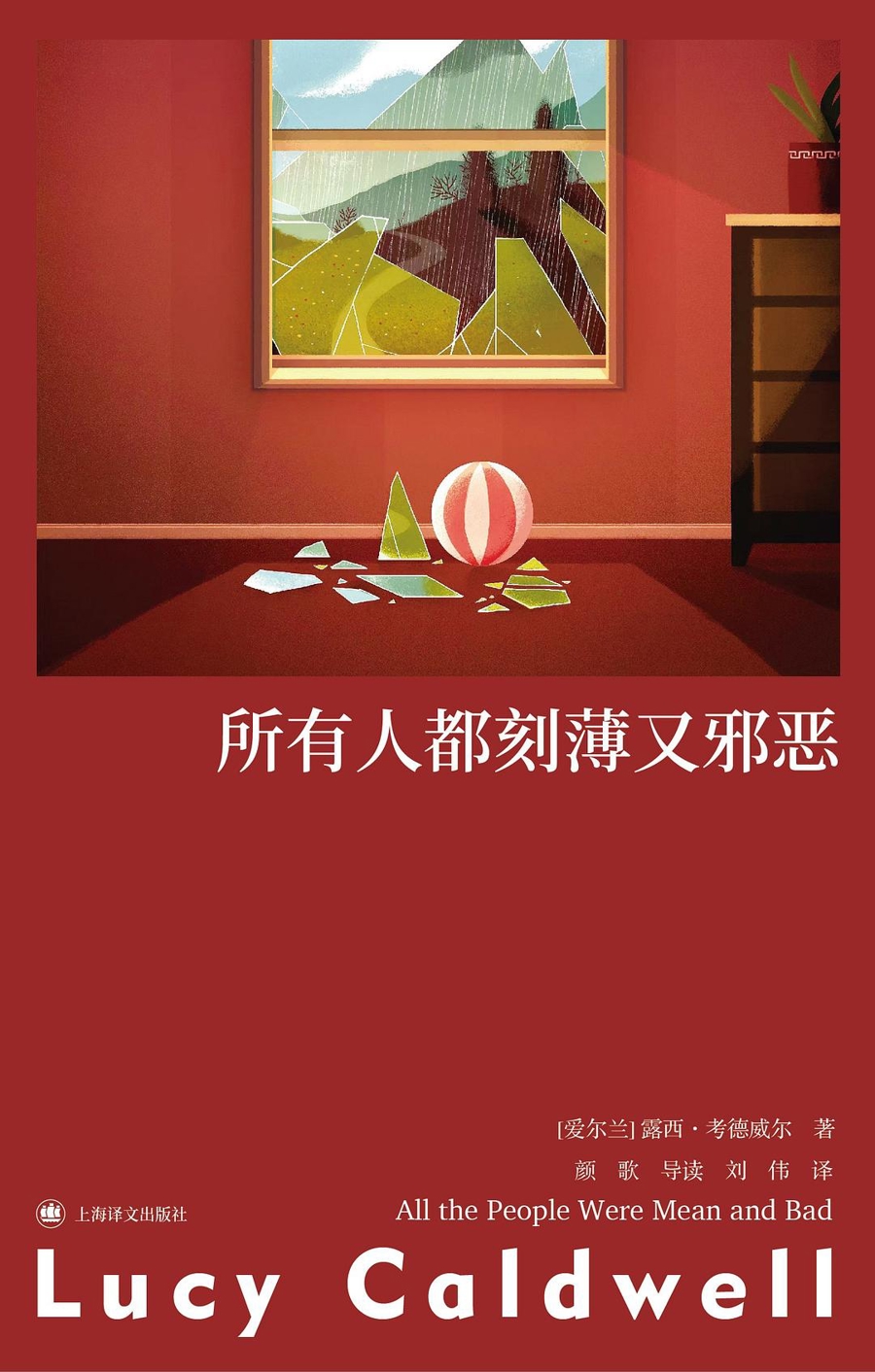
写作这些故事给露西带来各种文学奖项,但她更为触动的是,她带着小说行走世界各地,每到一处,当地读者、文学记者和评论家会用不同的语言和她分享:“我也有过类似经历,但是感到难以启齿,无法和任何人分享,你的小说让我意识到,我不是孤独的。”露西在十几岁时从贝尔法斯特到伦敦和剑桥上学,她的“北爱尔兰”身份让她很难融入主流,因为现实生活中的被放逐感,她会更关注那些“不分享,不谈论”的经验,她发现这些议题带着“羞耻的禁忌”,是被嫌弃的。当她写下这些不被允许进入公共讨论的主题,她从写作中得到战胜“羞耻规训”的力量。“写下来,让它们不再成为禁忌和耻辱。”这成了她的信念。
露西和旅居爱尔兰的中国作家颜歌是很亲密的朋友,她们聊过“作为母亲的尴尬事”,颜歌回忆她在哺乳期去斯德哥尔摩参加文学节:“一到现场我就感受到很多人戴着有色眼镜看我这个亚裔女作家,但这些跟涨奶的压力比不值一提,我在上台演讲前,手忙脚乱地去洗手间吸奶!”露西当即鼓动颜歌:“你把这写下来呀!还没有人在小说里写职场妈妈要吸奶这事多么困窘!”她认为,任何困扰着个体、却不能公开谈论的事件和感受,那些被主流轻视的“琐事”,值得在小说中被写下。她回忆十年前爱尔兰修改婚姻法案,保守派的电视台采访一个高龄老太,以为她一定激烈反对新婚姻法条例,结果满头白发的老妇人对着镜头说:“我支持。”她说她被传统婚姻困住,无法和所爱之人拥有另一种人生。露西看到这段采访,泪如雨下,她联想自己生活中遇到的想成为女人的男孩、不喜欢男孩的女孩、不愿进入婚姻的女人,这些人颤抖地生活在黑暗中,主流文学里没有他们的形象,这促使她写下《留在这个世界的理由》,这本小说集的英文原名叫《人群》。
“只要有人勇敢地写下‘不值一提’的小事,后续会有越来越多的作者加入。”露西回顾她写完《留在这个世界的理由》,主流文学中频繁出现这些议题:女性的性别认同、女性群体充满张力的关系、母亲和女儿的拉锯……以至于到今天,有文学评论家挖苦“女性题材翻来覆去写这些”,露西引用了西班牙加利西亚地区的女作家玛丽亚·雷蒙德斯的观点来反驳:“对于女性、少数族裔、弱势群体和边缘身份的人们,我们的抗争不是一场有始有终的战役。我们持续发声,就像妇女做家务,日复一日,家务活是做不完的。不存在被写得太多、写够了的主题,而是周而复始的家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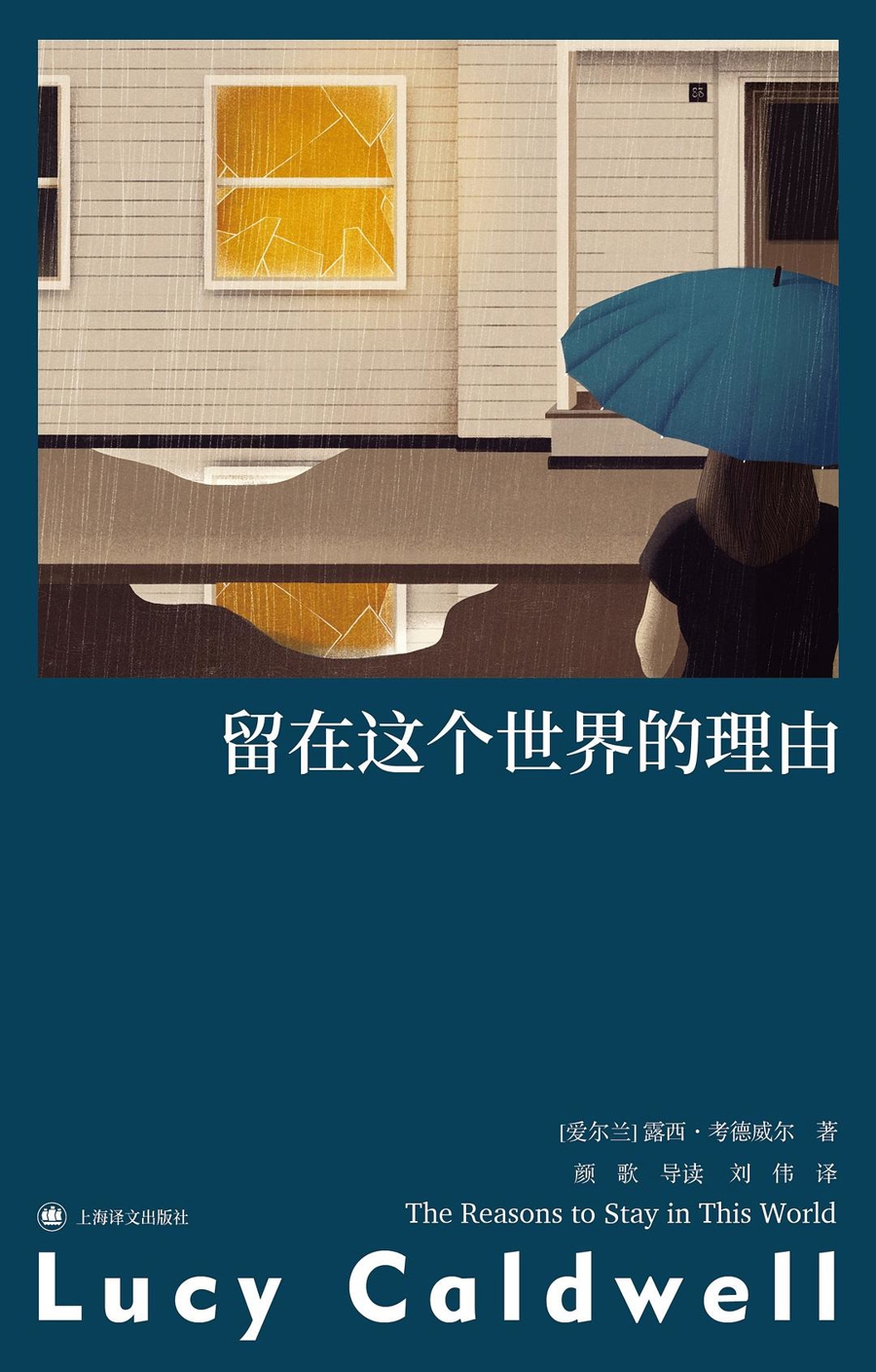
与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化学反应”
露西在上海的行程繁忙,她忙里偷闲地去吃本帮葱油拌面,给父亲买福鼎白茶,为女儿选玉镯,她喜欢中国文化,甚至打算和儿子一起学中文。她不像来自牛津的艾礼凯(《大理一年》作者),后者因为历史学家的父亲,是半吊子“中国通”,且在中国不同城市旅居多年。露西着迷的是两种语言、两种文学传统相遇产生的化学反应。
露西在短篇小说里创造了年龄、身份各异的主角们,然而这些小说分享了显著的共性,主角通常被特定的情境触发情绪开关,过往的时光和隐秘压抑的记忆在她/他的意识中再现,这些小说更像独白剧场,读者如同在黑暗的剧场中聆听主角“自己和不同时期、不同年龄的自己对话”。拥有小提琴学习经历、爱好古典乐的露西,在叙述中制造了记忆类同行板或慢板的忽快忽慢的节奏,时间成为塑造小说结构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英语明确的时态变化让读者无法忽略写作者在时间线上的清晰步调。而中文不存在变化的时态,翻译到中文的语境里,叙事中“过去”和“当下”的明确界限被模糊了,这加剧了小说叙述的不确定性,更突出了主角在内心世界的“漫游”,时间的线性特征模糊了,记忆是流动的拼图,过去与现在仿佛扑面而来,更有“说尽心中无限事”的私密絮语感。
露西喜欢这些语言和翻译带来的波动。她联想李白启发了庞德、庞德影响了艾略特、艾略特塑造英国现代写作,现在,“我的小说在中文里得到生长和发展,这也促使我从新的角度思考现代小说的技法。”
淘倍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